|
|
3#

楼主 |
发表于 2014-10-13 19:03:31
|
只看该作者
现将原编选者王启宏先生及笔者的注释之语一并附录于下(以王注和刘注来区分),供大家研究时参考:
(1)关于古代棋规出处
刘注:居荣鑫先生改编的《梅花泉》于1962年1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,约与此函同期,估计张公未及参看。居君在书中的“前言”和“关于古谱《梅花泉》”内均曾提到:“现在国内藏有该书抄本的,不过两三人,而海上藏谱家吴西都只有上、中两卷,没有下卷。笔者能够根据棋友萧永强的藏本加以整理、改编,并得到出版的机会,内心是兴奋万分的。”萧君于1963年之后下放农村劳动锻炼,经杨明忠先生荐介,按当时的较高市价忍痛将木刻本《心》谱和手抄本《梅》谱全集,割爱售给刘国斌,成全在下日后圆了“集清代排局四大名谱于一身”之梦。也为查考古代棋规增添珍贵资料。
(2)关于“久逼”及“二败”之惑
王注:此句录自《竹香斋象戏谱》,见《象棋谱大全》三集卷三第37页。
刘注:《心》谱内也称“无故久逼常将在二败之例”。常(今规称“长”)将、常照是同一个意思。“久逼”一词,不够严紧明确,系专指逼攻将帅而言,应包括长杀及一将一杀。“二败”即单方若走长将或长杀不变,两种均应判负之意。但在古谱操作中,对长将古今共愤一概作负;对长杀则不尽划一。原因是对“无故”二字的理解,颇有伸缩余地。何谓“无故”?怎么又算“有故”?这既与本方的窘迫状态有关,又牵涉到另一方的走子性质,畏首畏尾,那结论就很难下了。
(3)关于倡导加强棋例研究
刘注:张公胸怀大业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,幸而后辈不负张公至嘱,已百倍重视收集保存,整理利用棋例资料,从事专题探讨,进而著书立说,加强宣传,供诸参研,助推教学。个中,“棋例四友”业精于勤,颇见成效,名闻遐迩。不才笨鸟先飞,多年前即已在旧谱新书中遍插签条,以利寻求所需,并分类编册及广置卡片,备诸查选,自信解析棋例存疑已足敷应用矣。
(4)关于古局“长杀”判例
王注:指“野马操田”中先行方所采用的一种“长杀”着法。
刘注:见本文图1,重复着法为:红车三平一,里象7退9,车一平三,象9进7……红方长杀,黑方长拦,双方不变,古规作和(按与“二败”之说不符)。
(5)关于今规的“长杀”判例
刘注:即本文图2(规则原图亦仅半面无“将”)。着法是:红帅五平四,黑后车平6,帅四平五,车6平3……红方二闲,黑方一将一要连将杀(着法请爱好者自行演变,有助提高杀局功力),依六O中规,黑不变作负。张公借此说明今规与古规判例有所不同之意。
(6)关于企盼系统棋例早日成形
刘注:按照2004年象棋国家级裁判员再培训进修班举行时,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会掌门人所作题为“现代规则演进概略”的报告中所言:“于是,在1984年试行规则的基础上,五年时间两易其稿,产生了1987年中国象棋竞赛规则。八七规则在象棋规则理论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步伐,编写内容较好体现了依理定规,以规管例的指导思想……”设若22年之后这部聚全国精英智慧之力创制出来《规则》,果能获此名实相符的评价,则堪可告慰张公殷切期望之情了。
(7)关于棋图设计美中不足
王注:按原图,红方可以退车吃卒而成和。增一黑卒后,可避免此一变化。
刘注:见本文图3,红以车四平二,车二平四的一杀一将求和,实为拙思,何如立即用车砍卒成和来得痛快。添加6路黑卒档道,实属良策,红方只余犯禁作负一途了。但直至七五中规本图仍纹丝未动,既说明张公未及传达此项建议,也反映出建议者未能参与圈中,没有机会再表达己意。
(8)关于兵车相对能否算“兑”
王注:对六O规则图十二的修改意见是,取消红炮,增一黑卒,将黑车换成黑炮。×××认为;红兵的动作不是长捉,该算长兑。张雄飞认为:要解决此一问题,应先将“捉”与“兑”的定义解释清楚,六O规则内“兑是一对一的交换”,这个定义不严格,有修改之必要。
刘注:见本文图4。此项建议因牵连概念较多,故直到七五中规时才被采纳。捉、兑定义至关紧要,张公法眼如炬抓得很准。八七中规以“同兵种、有根子、第一反击能力、两个不致立即”的精准定义,锁定“捉”、“兑”不使相混。而九九中规却出人意料地以“兑是凡走子可与同等子力互换吃去者”的定性,返回到37年前张公不以为然的“一对一的交换”时代。其所持理由竟然是:“八七规则……有些文字显得言繁义奥,不易理解和操作”。可喜而令人感奋的是,O七中规试行本终于将“兑”的定义复归原貌,还原了学术真谛。
另外,能将兵捉车看成是互“兑”关系,还与把“同兵种”升格为“威力互达子”以及提倡“兵卒价值浮动”的思路有关,有的已经变成现实。
(9)关于禁着的最高指导原则与精神
王注:当时有两种主要的见解:(一)所以要有禁止着法的规定,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一方借此种着法纠缠成和。为了减少和棋的机会,禁止着法的面应该宽一些;(二)仅仅规定比较容易出现的长将、长杀、长捉、一将一杀(或一捉)等为禁止着法,而其余均不限。杀着的面窄一些,使居于劣势的一方可以努力寻求巧和的机会,也迫使已占优势,甚至是绝对优势的一方不能麻痹大意,有利于鼓励比赛时的干劲;同时,把《规则》如此适当简化以后,裁判工作上的差错亦可相应减少。根据张雄飞平日的谈论,他似乎比较倾向于(一),但认为(二)亦有其道理。
刘注:因雄飞先生仙逝猝然,并未赶得及在1962年11月合肥全国棋赛大会上,作出相关决议贯彻执行。以至迁延时日,多年来棋规棋例的通盘筹划始终处于摸索阶段。后经棋界同仁集思广议,从八四中规制订棋例总纲,逐步试行开始,日渐成熟,才使象棋规例有了统御全局的主动脉和权衡利害得失的价值观。此后与日俱进绵延至今。
关于“棋例”制订与实施的宽严倾向,笔者赞同雄飞先生禁例谨严的主张(实即“从重判处”的精神),这与防止消极谋和过多过滥的现代规则理念更为契合。当今正逢决定象棋规则命运的关键时刻,至盼在修订工作中严格统一标准,用同一杆秤衡量一切,勿枉勿纵,不偏不倚。否则,在“联合捉子”,“从捉到捉”,“兑献兼捉”,“净吃子”,“兵卒价值浮动限度”,“车与马炮互换关系”,“附带捉士相”以及“长打与非长打(建议恢复‘打’的术语名称)”等方面,各执一词,强词夺理,忽松忽紧,冷热不均,自相矛盾,永远“龃龉”不停,张公无法瞑目!(86)
(刘国斌)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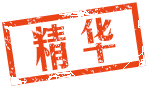

![]()

